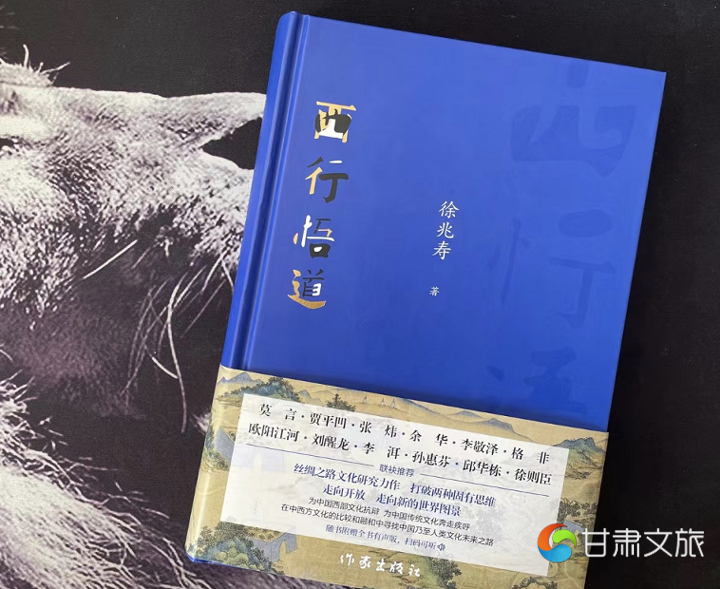
辩与问中重新发现徐兆寿
——《西行悟道》澳门品读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和解读是徐兆寿先生一直以来所专注的一个方向,在西北这座精神的高原之上,他默默的为此做着卓越的努力,并且成果斐然。从《荒原问道》到《鸠摩罗什》《问道知源》再到最新出版的著作《西行悟道》,他从西北出发,以笔为羽,穿大河,越群山,在这辽阔的旷野之地上,用文字为我们重新建构起中华古老的文明,特别是在当下的语境之下,我们如何拨开现代性的迷雾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徐兆寿用自己的作品为我们给出了可信的答案,他的新作《西行悟道》就是为此发出的一种呼声和呐喊。2021年12月22日,在澳门东亚出版社、《澳门社会科学》编辑部、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西行悟道》作品澳门品读会上,何平、宋明炜、曾攀、张定浩等著名评论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本著作展开了讨论。其中,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教授希望这本书能够被年轻的读者发现和阅读,因为这本书不应该只局限在学术界和文学界,应该有更多的普通读者去读,这涉及到西部在当代文化中间的意义和价值;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系主任宋明炜认为这本书也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学者所讲的“新唯物主义”书写,从国际视野来讲,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青年评论家、《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指出《西行悟道》既是想象西部的方式,也是对想象的一种反思以及反思之后的重新引导,与最近兴起的“新南方写作”可以相互参照;青年评论家、诗人张定浩谈到这是一本受众更广的书,它不应只是学术圈或文学圈的读物,而是一本可以让去西部旅行的人随身携带的、可以很好了解西部的普及性和导引性著作,本文将四位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辩与问中重新发现徐兆寿
——从《西行悟道》说起
何平
西,这个方位,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唐之际的玉门关,阳关以西,我们叫西域,比这个更早的就是所谓的西方和西极。平时大家最熟悉的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西游,去西天取经的西则更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现代话语中的西方出现了另外一个西方,和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的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在中国近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讲的西方,主要的是欧美的文化空间。故而,今天当我们谈论西方,其实存在着两个西方: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西方,另一个则是中国地理版图的西方。
刚才兆寿教授也谈到了对西部的感情。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兆寿教授所谈到的西方跟改革开放之前是有很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兆寿所谈到的中国西部或者“西方”,成为了不断激活中国文化的一股蛮荒之力,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绘画,不止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兆寿所说中国西北,包括西南。可以举出很多的案例,比如说第五代电影、绘画,比如音乐。自然地,文学的西部也一块有活力的版图,我记得当时有“新边塞诗”的提法,还有昌耀,小说里的张贤亮、张承志等等。
兆寿对西部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尤其是经过了他的文化旅行,从西部到了东部,即上海,从东部重新发现西部。可以想见,如果兆寿一直在西部,没有到东部旅行的话,他对于西部的认识,是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散文作家李娟,在新疆写作,她的散文最早被推介也在是上海。有意思的是,现在谈得比较多几个出生东北的年轻作家,首先不是在东北被发现、被强调,而是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在北京、上海被发现和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的旅行,从西部到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都市上海,又从上海回到了兰州,才构成了兆寿现在的整个《西行悟道》的文化路线图。没有这样一个地理空间的旅行,也不存在所谓新的文化视野。
具体到这本书,我是部分的认同于兆寿的观点。这本书的第一篇,是可以作为整本书的甚至是兆寿个人的文化宣言:“为古中国辩护”。为了辩护,他不惜不断用判断句来表达西部是什么,比如他说到:“西部是中国的古道,西部是中华文化最后的聚集地,西部是中国人的元气、自信乃至古老的血性生发之地”。在一系列的宣言里,最震撼我的是,“西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地”。近几年谈地域、谈特定的文化空间和个人关系的人,有两个人特别打动我,一个是阿来。他的《空山》,以“史诗”这种方式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有情的地景。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版《空山》,题目直接改为《机村史诗》。阿来在后记写到:“我是为亲人和同胞而写作的”,现在很少有作家讲自己的写作是给自己的亲人和同胞。当在谈及为何而写作这个问题时,许多作家都谈的特别的宏大、渺远,玄而乎之,但是当一个作家在谈自己为亲人和自己的同胞写作的时候,如果特别朴素,则自在动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到过西部的一些城市,但都是走马观花,我对于西部其实不甚了解。读了兆寿这本书,我才知道西部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他写西部的书共有13本,其实是在通过持续有力的写作来为西部辩护和发声。西部不只是中国地理空间的西部,也是文化的西部。这个西部,如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其文化源头的意义则更突出。所以,我也将兆寿这本书的为西部辩护,视为为古中国文化的辩护书。这本书还有一篇题目叫做《凉州之问》,其实,辩也好,问也好,都是一种辩护。
可以重点提及《寻找昆仑》这篇大文章,这在中国的当代散文中是很罕见的一篇,这个大并不是浮华的大,而是直击心灵的大。从这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兆寿的辩护之书,也是他精神成长的灵魂之书。兆寿教授充分扩张散文文体独特的魅力,也是在重建散文文体的尊严。今天讨论非虚构的人比较多,但非虚构有些部分是不能收编的,散文作为表达个人思想、呈现个人灵魂世界的独特文类,它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从兆寿所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为止,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个人精神的远征,正是因为这样的远征,这样一种成长,才带来了他为古中国、为西部、为凉州强有力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辩护。书中还有一篇名为《站在青春中国的门口》,当我们在《山海经》、昆仑山和一些中国古典神话中讨论西部,是貌似一种空间的概念,而在“青春中国的门口”讨论西部,则被赋予了未来时间意义。这里的青春,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或是生理年龄,而是中国力量的精神气质。虽然近几年我和兆寿教授的交流比较多,但当我读了这本书后,我还是要检讨自己,我应该把兆寿教授写西部的13本书都找来读一下,重新发现兆寿教授。所以从一个所谓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是要向兆寿道歉的。因为西部问题也是我近几年观察中国文学地图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在《花城》上做的栏目“花城关注”,2018年第六期做过一个专辑叫“文学西游或大于小说地理学”,我也跟译林出版社主编了“文学共同体书系”,所选作家都来自兆寿所辩护的西部,从这个角度来讲,兆寿的《西行悟道》中所悟的“道”,为我进入西部提供了一条“隐秘的心灵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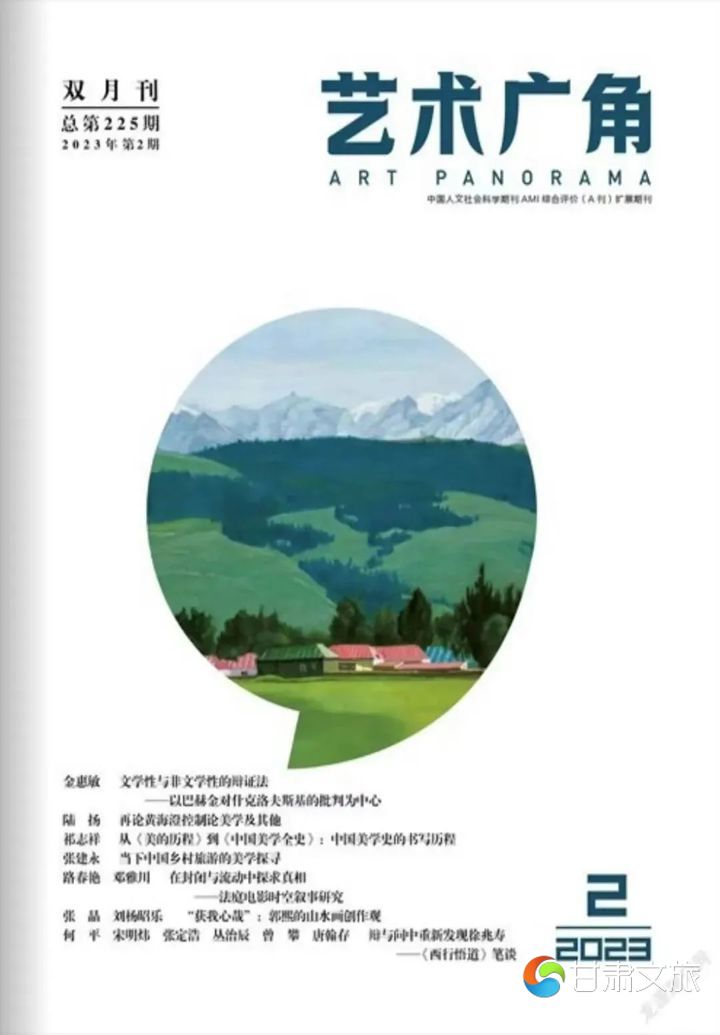

——本文刊发于《艺术广角》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何平:江苏海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曾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鲁迅研究月刊》《人文杂志》《钟山》《上海文学》等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近二十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转载和转摘。著有《解放阅读》《中国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散文说》等。主持国家、教育部、江苏省课题六项。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论文奖等。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