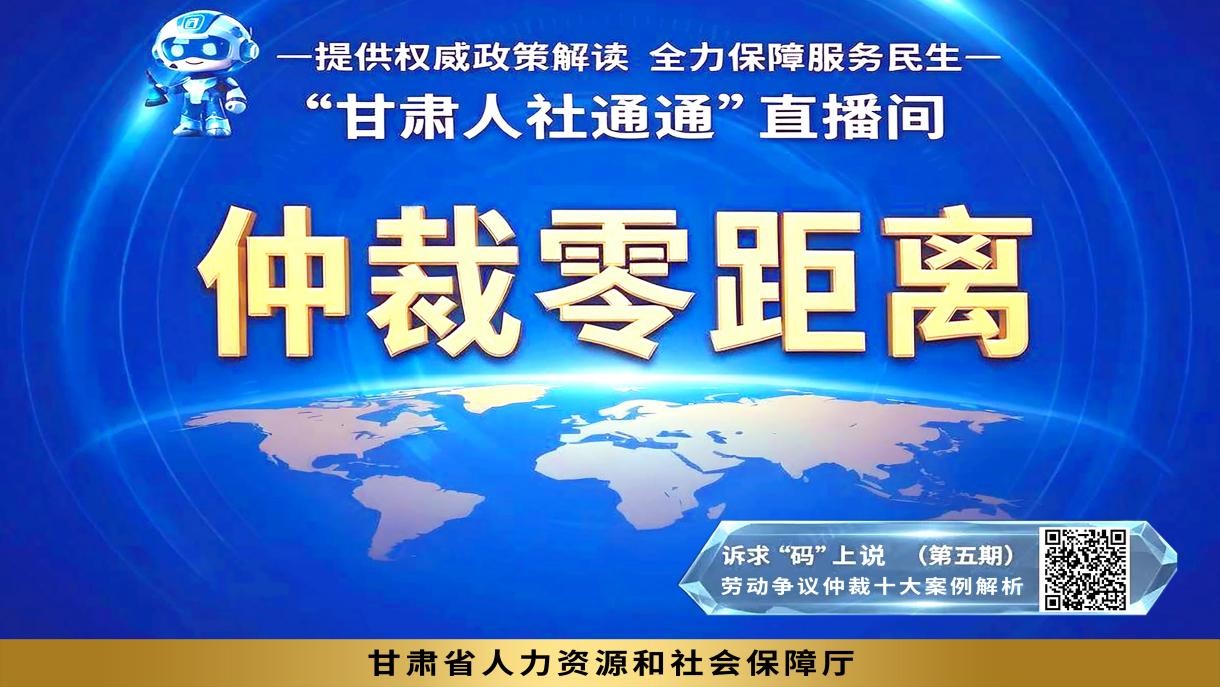/span>
/span>当我读到这些史记的时候,积石山大地上的麦子熟了三千多次,吹麻滩的金露梅开了三千多次。而大河家古渡口的木船,渡了芸芸众生。
大地上那些古老的事物,比如石刀、石犁、彩陶、玉器、铜器,在博物馆展台还是几千年前的样子。比如地名、窑洞、旧城遗址,还是古羌族的意蕴。大禹治水鲁班赶石的传说,还在积石山大地上一遍一遍流传。
其实,真正让人觉得岁月漫长的,是积石山的石头——那些冰川漂砾像羊群一样麻溜溜地卧在吹麻滩的河滩里,形成“石海”的震撼感、力量感,让人心生敬畏。
万年前的冰川运动不单单搬运冰块,也搬运船那么大的石头,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冰川把石头薅来薅去,低处的挪到高处,山谷的滚落到河滩,左岸的撞击到右岸。冰川才是真正的时空搬运工,冰川想拿石头把一条河钉住。
河水打磨石头,冰块打磨石头,光阴打磨石头,太阳和月亮打磨石头,把积石山的石头打磨成大自然原生态的样子。从远处看,真的像一群羊,羊背脊都一模一样。似乎放一条牧羊犬进到河滩,羊群会彼此起伏咩咩叫着逐水草而去。
吹麻滩的石海,是末次冰川运动的搬运,大约一万多年的历史。一万多年有多远呢?我总是走神,想到岩洞而居,结绳记事,草衣木食那样的时光里去——编草为衣,上树摘果子为食,远古的人类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
河滩里有一块传说中的鲁班石,石头上有一个石窝,一口大铁锅那样大。如果古人煮饭,就用那个天然的石头锅。如果古人想打猎,河滩里多的是石片,可以打造石头刀追击野兽。一万年确实久远,想一遍都想不周全。
找了巨大的一个石头,爬上石头顶,俯瞰吹麻滩河滩。那么多石头,白色的、青色的,能感受到强烈的气场。石头作为自然元素,是生命坚韧与大自然永恒的象征。吹麻滩的石头历经岁月打磨,呈现了一万年沧桑的模样。
除了石头,吹麻滩河滩里草木成片。草芽才发,树木才撒开叶子,河滩里一种绿烟朦胧的迷离之美。如果不是很忙,就找一块石头坐坐,晒太阳,听风吹,补一补天地之间的木石能量。石头带来的能量场,可以缓解日常疲惫。草木吐故纳新,能让人静心,剔除杂念。
草木把雨滴滤了一遍,地皮菜把耳朵贴到石头,雾气从吹麻滩的河谷里升起。过些天,犹如油菜田一般的金露梅就要盛开了。
大禹与积石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记所载,积石山是“禹所积石之山”。有学者认为,大禹的出生地在河湟流域的古河州,即今天的临夏州域内。
古籍记载:“禹兴于西羌。羌,西域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大禹在黄河上游治水,积石成堆,成为今天的积石山。山川留河,树木留根,人留地名。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地名,都是历史文化留下的标记。名字是万事万物的灵魂,在时空中留下自己。想来能够积石成山命名的,只有大禹了。
民间传说里,禹王爷导河消除水患,从积石山开始,劈开峡谷,开凿成一条石峡,黄河顺着石峡东流而去。那条峡谷就叫积石峡。河水拐来拐去,动不动发洪水,大禹想拿积石山这个名字把河流钉住。
如果说大禹治水是宏大的历史叙事,那么积石山是对历史叙事的一个回应——这个地方,你来过。这条河流,你治理过。这些石头,你看到过。这片土地,你走过。
我总是有一种画面感:大禹停下凿山的斧子,直起腰,看着远处涛涛黄河。他能感应到天地之间的细微变化,哪怕是石头掉落的喀嚓声,哪怕是树木摇摆的窸窣声,哪怕是羊皮筏子穿越黄河的哗啦声。他往积石山的山顶上走去,翻过一个又一个大石头,绕开藤草,风吹着他的衣衫,疾步走到高处。
如果临夏是他的出生地,那么这片土地就是全世界他最喜欢的地方。如果他要到别处去工作,那么最原始的治水经验就是从这片土地积累出来的。
山顶的禹王爷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听到山下黄河的水的撞击声,哗啦哗啦。他就那样,停在四千年的时空里,鞋子踩在土地里,弯腰捡一块石头,衣襟被风吹着,一动不动。这是我想象出来的雕像,如果我是雕塑家,就用积石山的石头,雕刻出这样一尊禹王爷雕像。
在积石山,我们去了好多地方,大河家镇,刘集乡,胡林家乡,河崖村,团结村,康吊村,四堡子新村……微风吹啊吹啊,杏花漫山遍野,开得所向披靡,村庄像在油画里,美得像一首首诗歌。喜欢村庄里的榆树,枝叶拂拂,榆钱的清甜味道在风里飘荡。雨点落到山谷,山野里艾草、矢车菊、马齿笕,都在迎风长高。雨点已经不是三千年前的雨点,石头却还是一万年前的石头。
走在田野里,找到古老的雅韵,像古人那样大声唱:积石成山,积雨成河,草木生长,五谷丰登。
在梅坡村,遇见杏花,一下子遇见春天——漫长冬季寂静之后的喧闹。
一坡杏花开得所向披靡,粉色的云朵一般,突然就理解了枝头春意闹美好的意境。一时有些蒙圈,想不起来一个合适的词儿来面对如此盛大的花朵。脑子能想起来的,是小视频里那个沙哑而惊喜的声音:快来看,花开啦……
花开得越是阔绰,词儿越找不到。车马春山慢慢行,春山一路鸟空啼,暖茶对春闲——这些都想不起来,就想起来那个狂喜的声音:快来看,花开啦……这一嗓子吼得又直白又开心。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这两句也没想起来。因为山野里,花影重重不用童儿扫呀,花开花落,风来风去,全是逍遥自在。
是的,花开就会花落,大地上的事物没有什么能恒久不变,时光万物都在流动。花落也不必伤感,有花有果,花落果实就会冒出来,结出一枚一枚的青杏儿。
杏花枝头上,是微风疾走的簌簌声。如火如荼的杏花包裹着山坡,偶尔有鸟啼划过。繁花漫过山坡,漫过花影,漫过荒草,一枝挤着一枝微微晃动。梅坡村,这个名字多么好,诗经里的那种悠然雅致。
山野看花,就看个随心自在。一山一野的花儿,风一吹,花瓣翻飞,一坡一野全是淡粉色花瓣。其实你想想,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风景,不一定遇见梅坡的杏花。但是我多么幸运,一下子就遇见梅坡村一年里最美的时光。
我觉得枝头的杏花一边开一边唱歌,只是花朵的歌声我们听不到罢了。花朵的歌声像风笛声那样,传递到风中,大地上的草木击掌而舞。
在梅坡,看花,晒太阳,远处是黄河,滔滔而去。正午的太阳很热,阳光冲着山坡和摇曳的花枝,热烈地照耀。树叶子才撒开叶子,新新的一种绿。荒草里草芽也才蹿出来,吐故纳新。石头缝里,小草也挤出来,迎风摇曳。这草木,现在荒寒,但是过些天来看,早已经郁郁葱葱,绿得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鸟鸣声依稀可辨。如果时间宽裕,就在树下坐下来,翻开一本喜欢的书,慢慢读。花瓣像粉色的小鱼儿,游弋在书页上,头发上,山坡上。阳光穿过杏树枝叶,穿过一簇簇花朵,筛在树底下,花影重叠。
在积石山,没有一个村庄是不开花的。春天的花朵从一座山传递到另一座山,从一个村传递到另一个村,从一棵树传递到另一棵树,从一个枝头传递到另一个枝头,齐刷刷的,说开都开了。春来春去花知道。
除了开花,榆钱也披拂飞扬。
克新民村的午后,一阵风吹过,干燥的热。村口的一棵老树,老树下有石磨、石碾,还有一些农具。打眼一看,就有乡愁的味道。榆钱很多,我觉得这个村子好阔绰,头顶上全是钱串子。
榆钱这个名字很好听,阔气得很。村子里走一走,全是钱串子在随风而晃,瞬间觉得也是阔绰的人了。看见榆钱,就想起古人的钱串子,在枝头晃呀晃,相互碰撞,哐啷哐啷响。榆钱的绿色不浓,是一种淡淡的黄绿色,很干净的绿。
捋了一把榆钱,嚼,有点甜味。朋友们说做了榆钱饼子很好吃,我没吃过。我小时候家里爱吃苜蓿,整个春天似乎都在吃苜蓿。村子里也有榆树,但是没吃过榆钱。可能我们村的人只喜欢苜蓿。童年后遗症就是看见苜蓿地,就手欠,想掐一把带回家。
要是想吃春,就吃点榆钱苜蓿苦苦菜啥的,是春天的味道。
我们在村子里串门,遇见的人们都很热情。大家忙忙碌碌,春天是庄稼播种的季节,充满了一年的期待和希望。
一路走,到了临津古渡口,一个古老的黄河渡口。晚春时节,黄河水清亮亮的,带点绿意。古渡口的铁索掠过黄河,一座大桥横跨黄河。铁索和大桥的影子,被太阳画下来,拓在宽阔的水面。如果在月夜,就会在河水里看到月亮,黄澄澄的,随着水波荡漾。
桥对面就是青海,山是赭红色的,像一把很大的扇子。可以在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甘肃,一会儿在青海。
临津古渡口很有历史。霍去病、隋炀帝、文成公主,都是从这条渡口路过的。古时候茶马互市,茶叶和马匹就走这个渡口。有学者认为,临津古渡口是大禹治水的源头。
我在黄河边捡石头,像一只铺开翅膀的老鹰。石头缝隙的水洼里,很小鱼儿游动。人类的世界是世界,石头的世界是世界,鱼儿的世界也是世界。如果有羊皮筏子横渡黄河,有一曲“花儿”漫过黄河,那该是怎样的诗情画意啊。
好看的石头很多,颜色也很柔和。鞋子有点滑,得小心翼翼溜达。有一块青绿色的石头,太大了,拿不动,找了个小圆石头。石头寓意时来运转,会带来好运气。
大河家的街道繁华热闹,店铺里人声鼎沸。中午在一家面馆吃饭,客人多,看不到空座位。大河家的面食好吃是出了名的,盖碗茶也很有特色。
感觉大河家比别处热一些,路边繁花盛开,树叶子全都绿汪汪的,冬小麦已经一乍高,遮住了麦地垄。我们去了养牛场,去了蔬菜种植大棚,所有勤劳付出,都会有丰硕的收获。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