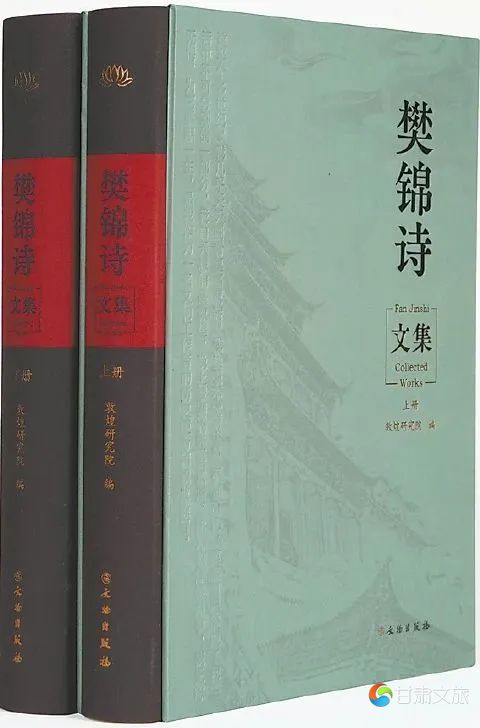
《樊锦诗文集》樊锦诗 著 敦煌研究院 编 文物出版社
我与敦煌结缘始于毕业实习。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年,按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要参加毕业专题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格外向往的地方,因为中学时曾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从此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考入北大念了考古专业之后,凡是有关敦煌的信息和事情我都格外关注。毕业专题实习,我如愿到了敦煌。想象中的敦煌,是一个超然世外的桃花源,谁知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走出洞窟,竟是满目荒凉,周围是戈壁沙漠,交通不便,环境闭塞,无电无水,喝苦咸水,伙食不好,生活艰苦。由于水土不服,我实习只进行到一半就离开了敦煌。没想到第二年毕业分配,又把我分到了敦煌。这一来,我竟然在敦煌工作生活了六十年。
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一直没有做“四有”中的“科学记录档案”。1978年,我建议并主持开展敦煌莫高窟“科学记录档案”工作。当时莫高窟北区洞窟尚未开展考古工作,南区有492个洞窟,就要做492本档案。每本洞窟档案,都要有简单的洞窟平面、剖面图,有简明的文字,说明洞窟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保存和保护现状、有无损坏和病害,还要有洞窟照片。这项工作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来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我先后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担任副院长后,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申遗”。198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莫高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我负责撰写莫高窟的“申遗”材料。“申遗”材料涉及面广,要求高,于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改革开放与敦煌研究院扩建的大好形势,激励了莫高窟人努力奋进,实现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我深深意识到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与保护技术上,被动地跟着病害文物做修复,无法达到对石窟的有效保护。要做好莫高窟的保护,离不开科学技术。20世纪80年代,我推动敦煌研究院与国内科研机构横向合作,申请国家拨专款购买科学仪器和现代化设施,那时的研究院已有了做材料分析的X光衍射仪,安装了现代化监测系统。与此同时,1986年与日本国立东京文化财研究所、1988年与美国洛杉矶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始合作科学保护,并合作培养科技保护人才。在合作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保护科学实验室,配备仪器设备,增添科技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由此进入预防性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北京出差,偶然看到了在电脑上展示图像,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可以永远不变的信息。进一步咨询后,建议在莫高窟尝试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敦煌研究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集图像采集、数据加工、安全存储和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壁画数字化关键技术与流程规范,开展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工程。我提出了“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想法。这项工作是重要的预防性保护,成为敦煌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未来长期的使命和职责。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建成了“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并将30个典型洞窟的高清数据在互联网平台向全球共享。
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立足长远和全盘统筹谋划部署。我们敦煌研究院与中国建筑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等密切合作,吸取国际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先进理念、先进原则,起草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
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上有些人来游说我、动员我,让莫高窟参与投资,入股、上市,来势汹汹。为了顶住这种风气,我只有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执笔起草了《保护条例》的草稿,提请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明确了莫高窟保护对象、范围,规定了敦煌研究院的职责,及其保护、利用、管理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也明确规定了政府部门的职责。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发现社会上出现滥用和盗用莫高窟文物资料开发售卖商品、恶意抢注敦煌文物商标等不良现象。我带领相关同事很快采取了维权措施。2000年9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委修改《文物保护法》调研组座谈会上,我代表敦煌研究院发言,提出了文物保护一定要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2003年颁布实施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机构对敦煌莫高窟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其提供资料制作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产权。”
进入新世纪,适遇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莫高窟的游客超速递增,给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压力。一定要做到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合理利用中做好文物保护。实施“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既保障了洞窟文物安全,又满足了游客参观的需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不是几代人、几十年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代一代“莫高人”不断坚守,持续传承、努力和开拓。从事业务和管理六十年,我回头看这几十年写的文章,文集中收录的一些篇目谈不上是什么治学,有些只是粗浅的感悟、思考和介绍而已,希望能给诸君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作者: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来源 :北京日报副刊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