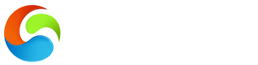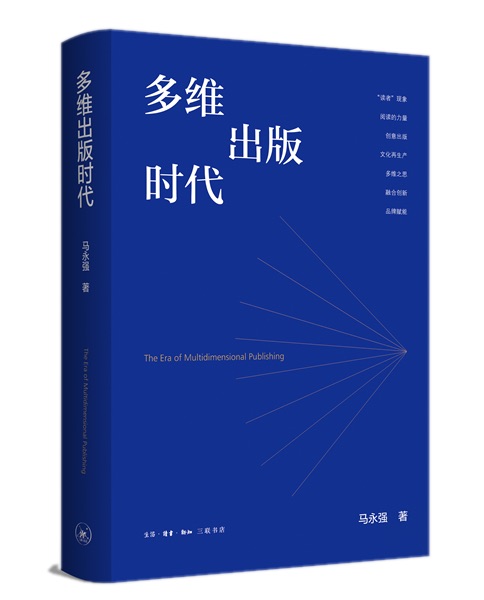高天厚土 多彩庆阳
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签约作家走进庆阳采风创作活动作品选登
编者按
2025年7月10日至14日,由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庆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高天厚土 多彩庆阳”采风活动成功举办。其间,作家们通过采风,对庆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多彩的自然风光、繁荣的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
子午岭笔记
禄永峰
合欢树
山洼地带,我看见一群榆树,有七八棵,树梢靠拢,像是埋头在窃窃私语。而这几棵树的树身,个个扭动得厉害,有几棵树的树身从根部开始猛地“折”了一下,长了一截,再“折”一下。本就不高的树身,出现两三“折”,让人看着都疼。还有两棵树,尽管没有“折”,但整个树身匀称地朝别的树梢稳稳地爬过去,长成了爬行着的树。
一圈榆树树身和树梢,都使劲地朝向中央地带靠拢。几乎每棵树树身的内侧,都没有长枝,而大多大、小枝,都长在树身的外侧。一圈树的枝叶稠密地把中间地带的空地包围着,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一块硕大的树冠,盖在大地之上。
树与树相遇,交流最多的恐怕就算是地下的根系和空中的枝叶。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像人类一样轻松识别同类。地下的根系相遇,若是同一种类树的话,它们是根根相残,还是善意避让。在森林里遇见各种各样的树多了,类似这样有趣的问题不是由自己提出来,而是生长着的树在不断地能够启发自己。
我遇见一棵有七八百年树龄的老槐树,它生长着的一面土台坍塌,粗壮的树根暴露了出来。从每一条根系的走势看,它们脉络清晰,并未出现根系交叉或者缠绕的情况。这是同一棵树,它把根系的生长痕迹真实地展示给遇见它的人。而同一种类或不同种类的树相遇,它们的根系又是以怎样的情景运行呢?但可以肯定的是,同一种类树木的树梢相遇,它们会不约而同地朝向中间靠拢。
除过我遇见的七八棵榆树树梢长成“一个大树冠”外,我还在山林里的一块台地上遇见过四棵槐树。远远看去,那就是一个非常茂密、酷似一棵大树的树冠。当我来到树下时,才发现自己从远处看到的超大树冠是由四棵国槐树树梢一起组合而成的。这四棵树,每棵树的大枝都朝外延伸,遒劲有力,而遇到相邻的另一棵树的树枝,都回避朝上生长,四棵树之间并没有出现相互碰撞。而它们真真切切地长成了一个“共同”的树冠,它们的生长似乎在同步进行。或许是为了一起长得更高大,每棵树树身都稳稳地朝外倾斜,而树梢共同朝向中间靠拢。
走过一片松树林的时候,松树在林里长得更加高耸、挺立、密集,但是相邻的松树之间,松针很少触碰在一起,枝梢也很少触碰在一起。在密集型的松林里,松树与松树似乎懂得避让,它们看似各长各的。原本,我认为的树邻之间会进行的生存竞争,实则它们在一起的环境里懂得相互避让,没有看到同类相互伤残。
不难推断,树木抱团抵抗一场风,远远胜过孤树作战。若是一场狂风袭来,一棵孤独的树或许会在大风中折枝,甚至连同一棵树身掀折。这类情景,每年在林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而树木群立在大地之上,树木的枝叶在风中碰撞擦伤的概率就会大大地降低。
每一棵树,看似“看不见”同类,但是它们能够轻松地通过地下根系和空中的枝叶“摸得着”对方,这是树与树具有的识别能力,是生而具有的,默默隐藏在每一棵树的根系、树身、枝叶之中,它们凭此识别自己,识别同类。甚至,它们始终都将所有的树木都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永不分离。
在树林里,我还遇见过三棵杨树,它们像是同一个根系,挺身而起,抬头仰望,像插立在大地上的三柱长香,与婆娑的绿叶一同直穿云里。我所遇到的这些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合欢树。

子午岭 水天一色
树的倾斜度
我在甘肃子午岭林区发现的树,它们大多都具备朝上生长、保持直立的特点。不论是在平坦地带,还是在陡坡地带。直立的树,撑起巨大的树冠的力量都源自树干部分。立木顶千斤的原理,就是来自一棵棵直立生长的大树。
先前我去过不少次大凤川。大凤川属于子午岭林区。大凤川湖畔边的坡地上,有一大片白桦树。白桦树的树冠并不大。树身上露出来的黑色结疤似一只只黑色的眼睛,一个个争相朝我看过来,可爱活泼。尽管树身只有碗口那么粗,但它们总是保持着直立生长的姿势。
法国作家雅克·达森在《植物在想什么》一书中提到:树似乎遵守了“保持直立”的强制性命令。但树生长在一个充满了不规则、不确定外力因素影响的环境中,保持直立成为树的一项艰巨而持久的挑战。的确如此。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树的直立生长会受到挑战。夏天的几场大雨过后,我再次来到大凤川湖畔,我所邂逅的那片白桦树林,一律朝山坡下微微倾斜着,所有白桦树倾斜的方向不仅相同,倾斜的夹角度数也几乎一样。我在一处滑坡的地方发现,裸露在外的新鲜地皮的湿度并不厚,几棵树根部都是新的干燥的黄土层。陡坡上的白桦树,在暴风雨中倾斜后迟迟没有直立起来,问题应该出在了它们的根部周围的土壤。我相信,由于树木能够感知到重力,重力作用下它们能够感知到垂直度。这些倾斜的白桦树很快能够直立起来的。
立秋后,雨水减少。我再次在大凤川看到那一片白桦树林时,它们的树身的确调整了过来,一棵棵都直立着,偶尔有几枚树叶在秋风里落下,轻轻地,听不见一点声响。寂静的树林里,我们看不见树木之间的抗争。事实上,树与自然的斗争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外部的树干、树枝、树梢和一枚枚叶子,还有藏在暗处的根系。
在林区我遇见一棵长在悬崖上的树。那是一棵椿树。树干垂直悬崖向前长了不足一米,又果断地朝上折去,最终看到这棵树的模样,树干保持着直立,枝繁叶茂。因此,从这棵悬崖上的椿树的长势看,树木受到外力或者重力的影响,具备柔韧性和自然修复的能力,自我调整,很快能够让倾斜的部分恢复到原来挺直的位置。阔叶树如此,针叶树亦如此。
树木的直立性和自我修复,在松树林里尤为如此。没有哪一棵松树大幅度地倾斜。一群松树相遇,树梢挨着树梢,树干距离一两米,笔直地朝着头顶的太阳奔赶。十分专注。谁也不让谁。争相朝着头顶的天空直直地钻上去。追逐头顶的阳光、蓝天和浮动的白云。而树身下部先前生出来的枝条,一点一点干枯、脱落。脱落后留下的枯枝长短不一。每棵松树把所有的养分都朝着树梢供应,全力完成生命的冲刺。我想,哪棵松树若不是生长在松林里,它的树身和整个树的高度,必会与松林里不同。甚至被一场场从山脊上、山沟里滚动而来的大风掀着长成了倾斜的树。
北方,风多,风大。移栽在城里的松树、七叶树、国槐等树木,匀称地栽植于街道两侧,在成为一棵大树前,四五根撑杆围绕树身撑开——扶持幼树走一程。还有被移栽的大树,国槐、油松居多,树根看似带了硕大的土球,可在城里站不稳,仍然得靠几根撑杆挟持着,在风里扎根。几年之后,待树木在风中能够独自立得稳,园艺工人才解开绑缚于树身的撑杆,让其自由生长。
看来,树木成木、成景、成林,得靠树木自己,还得依靠人类成全。

子午岭 连家砭林场日出
树瘿与水泥
再看一棵古槐树吧!这棵古树在甘肃宁县盘克镇宋庄村。
古树动辄长几百甚至上千年,仍然安安稳稳地直立在大地上,一副不愿败给时间的模样。抵达一棵树的内部,我不想查找关于树背后的史料记载,也不想听关于一棵古树背后谜一样的传说。我只需来到树下就足够了。摸一摸树身,闻一闻树枝树叶的气味,仰起头来环顾一遍树梢的走势。然后找一块地方坐下来,发一会儿呆,让风吹树叶的声音,声声入耳。
这棵古槐树,与其他古树不同的是,它的根部有一处巨大的树瘿。像一块巨大的肿瘤,与树浑然一体。树瘿是树身上凸出来块状的疙瘩,紧贴着树身。有点像古人结绳记事。树瘿是树受到过的疼痛,树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树的疼痛,可能是病虫害,可能是人为破坏砍伐,也可能是哪一根树枝在暴风雨中折落。
不难发现,我眼前的这棵古槐树是遭受过疼痛的。从树身上部开始分开枝杈的地方,先前是有三个主枝,有两处主枝枯死多年。树的生长,养分是从根系通过树干、主枝、侧枝、枝梢一路供应的。有两根主枝枯死,我猜想一定是枯死的主枝连接的树身出了问题。果然如此。我的视线朝着树身渐渐滑下,树身上有两段树皮不知道在何时脱落,露出树的木质层。树皮是树的衣裳。无论什么树,从一棵幼树到一棵古树,树的衣裳始终相伴。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古树,它们的衣裳不再光滑和青绿,整个树身上满是隆起裂开的木棱纹,纵贯全身。粗糙的纹理条条竖向生长,手掌轻轻地抚摸过,宽深处可以没入手指,一直延伸至蓝天白云里,满满是岁月的沧桑和风雨前尘。
一棵树在生命的历程之中,树的衣裳除过人为的破坏剥离外,大多会是雨水浸入树身,破坏树的木质层甚至坏死。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树身虚空了,树身由内而外溃败。
有两段树皮脱落的这棵古槐树,枯死的两根主枝明显是人为处理的。两段树皮从树杈到根部,平平地“铺”了下来。我放大拍摄到的图片,那两处枯枝明显是经过“截肢”处理过的。好在截肢后的树冠部分生出了许多新枝已经铺展了开来。这些新长开的枝条又有了新的分枝,形成了一棵树完整的树冠。若是不到树下细心分辨,竟然丝毫看不出来。
自然,这是一根枝繁叶茂的老槐树。
没有谁关注它曾经走过的路,没有谁关注它曾经遭受过的疼痛。
或许由于它是一棵古树,近年才被附近的村民格外“呵护”——人们给脱离树皮的地方,涂抹了两指厚的水泥,直到根部;而树根周围,又专门围绕树干修建了一处花园式水泥砖护栏,靠近村路的那面树根部,有一截树根已经触破了水泥护栏,像是一块骨头冒出来——有一半身体枯死而疼痛的树,它的根系还在大地之下继续延伸,没有停止生长。
至于人为在脱落树皮的地方涂抹一层水泥呢,我想,不管这种做法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有效阻止雨水淋湿木质层,防止裸露在外的木质层一点一点在时光里朽坏。
靠近树身,手再次抚摸过,水泥,是冰冷的,但留下来的树皮,粗糙、温热,树的体温,人一定能够感知。阳光从枝叶之间洒落下来,我双手合十,替一棵古树祝福、祈福。

秋色初染小凤川
树的几种非正常死亡
在子午岭林区深处,路过湖边的时候,我的目光被湖中央的三棵枯树吸引了过去。水里的树,不知道是哪一年死的。从枝梢到树身,脱了皮,白色的木质层裸露着,像光一样刺眼,倒映在水里,纹丝不动。从粗壮的树身判断,这是一棵至少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树。枝梢部分的细枝已经被风吹折,眼前只剩下比较粗的几根主枝,连同树身一起插在湖中央。
我在湖畔凝视那三棵大树,在我的理解里,这应该算是溺水而亡的几棵大树。算得上是树的一种非正常死亡。湖面从低洼地带延伸到远处。看湖面的走向,先前这里是一条小河,树长在小河边。临水而生,树自然茂盛高耸。只是后来,人为控制了流水量,让小河沿两边漫延开来形成了人工湖。湖里养鱼。树也被“养”了进去。人都说水火无情,对于一棵棵水中央的枯树,无情的显然不只是水。
若不是溺水而亡,树会自然生长。谁也无法估量一棵树的生命长度,树把一切都交给了蓝天里婆娑的枝叶和大地下盘绕的根系,包括人类。
在树木的种类里,大多树发木较慢,而快的,比如杨树、柳树,不多几年,绿荫盖天。发木较快的树木木质不够硬。多年的老柳树,几乎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我童年所遇见的一棵老柳树,据说有几百年的树龄,树身低矮,枝梢像掉毛的火鸡,稀稀落落的。就这棵树,每年春天里绽出的新绿,都是贴着干枯的树身长出来的。居住在老柳树附近的老人们说,柳树顽头好(顽强的意思),有几年树身在大风中被吹折,但来年还是活了过来。走近树,它的树身一侧有一大块空了,一个孩子可以钻进去。钻进树身里,头顶丝丝缕缕的亮光从老柳树树身的枝杈部分漏下来。半明半暗。大人禁止孩子钻树身,说树身里有蛇。雷雨天,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噼里啪啦的雷声劈开老柳树,树身里就钻出来过蛇。听着扣人心弦,不过这都是人们传下来的。
若与火相遇,木质再硬实的树,还是难逃一劫。村里一棵六百年的老槐树,距离根部的树身一侧长空了。一个成人侧身钻进去,脚手蜷缩,能够藏得住。一年冬天,有个流浪乞丐看好那块树洞,夜晚时分常常到此隐身避寒。树洞透风,乞丐便在树洞口燃起一堆柴火。树洞内层木质老朽,树身内部还有拳头大的小洞窜到了枝杈部分。遇到火,树身内,恰似烟筒,树洞口的火苗被一股脑儿地吸了进去。乞丐见状不妙,爬出树洞,逃之夭夭。村人赶到用土、水扑火,经过八个多小时,才将树火扑灭。
一场火攻击到了树木的内部,树身和枝梢毁于一旦。
若火从外部而来呢,树一样会被活活地烧死。在一个村庄,我见过一棵被火烧过的树。村里人说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从庄稼地里清理的柴火围绕树身胡乱堆积着,孩子点燃柴火,整棵树被熊熊大火紧紧地包围。好在村庄人发现赶来将火及时扑灭。但那棵树呢,被火烧黑的树皮渐渐全部脱光了,树身上的木质层,有好多处留下黑乎乎的疤痕。风风雨雨几年后,黑色的疤痕仍然很是清晰。有几处枝杈处也黑乎乎的。这些黑色的部分,都是火烧树木留下来的证据——树毫无遮掩地替人记住了一场灾难。
这便是我近年所邂逅的树的几种非正常死亡方式。我替树记录下来。
作者简介

禄永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签约作家,第三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作品入选中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和多个选本,被《散文选刊》《作家文摘》《海外文摘》等转载。曾获孙犁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人民文学》杂志征文奖等。出版散文集《风吹过村庄》《草木之疼》。 来源 :庆阳文学院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